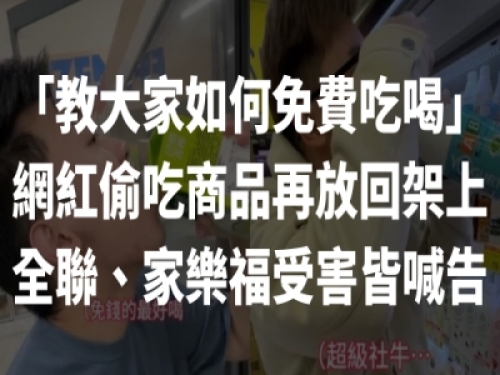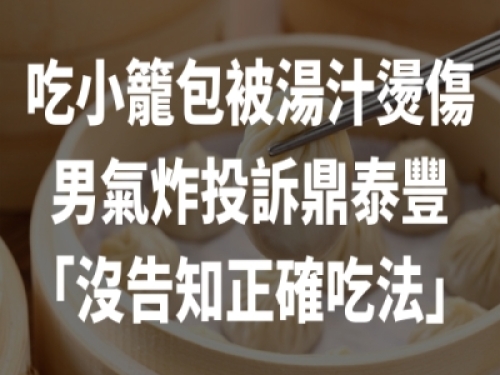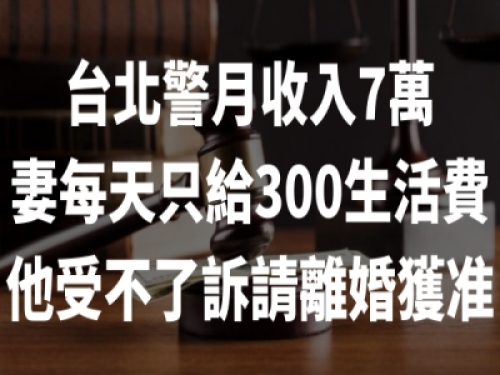骨子裡的優雅,是於無人見處,也能精緻待己

前兩天在雜誌上看到了一篇關於卡門·戴爾·艾麗菲斯的報導,眼睛還徜徉在文字裡,思緒卻飄到一個老太太身上。 這件事兒說起來有點難於啟齒。
我讀書的時候,家裡很貧困,生活費常常捉襟見肘。我們宿舍的一個女孩見我狀況如此窘迫,便跟我商量,每週六、週日去照顧她的奶奶。
管三餐,住一晚,薪酬也不錯,而且還在休息日,除了是因為同寢的親戚這一點有些尷尬,其他都適合我,畢竟這比我去陌生家庭做家教,教導一個陌生的孩子要輕鬆安全得多。
第一次去老太太家,還沒見到人,我就被她的家打動了,不是多麼豪華,而是那種令人眼前一亮,清新爽目的整潔。
一律白色的家具,地板,大青花瓷的瓶子裡插著艷紅的玫瑰,淡黃色淺粉菊的壁紙,一塵不染,那種整潔甚至令人感到距離和不可靠近。我正猶豫,同學喊姑奶奶,一個老太太應聲而出,她坐著輪椅,杏色的針織罩衣,米白色的睡袍,滿頭銀髮,戴著水晶眼鏡。
她一邊往後託了托垂落在耳際的兩縷捲髮,一邊翹起嘴角笑著說:“去收拾了下。”很明顯的化了妝,胭脂腮紅,還有殷紅的唇色,但和她滿頭銀絲配起來,很好看。我從心裡讚歎了一下。
同學說,奶奶,您都夠漂亮了,還扮得這麼美,想迷死誰啊。看樣子她們經常這樣開玩笑。老太太慢條斯理地說,不為迷死誰,我得先讓我自己著迷。
我一愣,覺得這老太太說話很不同。又覺得她打扮得這麼漂亮來迎接我太隆重,心想,可能獨居的老人,過於單調寂寞的日常,見到陌生的人,這般費心裝扮自己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發現,老太太這樣完全不是因為我,精緻打扮,是她的家常。
那天早晨我準備好了早餐,等了一會兒,見她沒到餐廳來,便去尋她,看見她正坐在臥室的梳妝鏡前,精心塗口紅。
我倚著門框說,您的妝畫得真好看。我好不好看呢?她扭過頭來,微笑地看我,甚至眼神裡有幾分孩童的頑皮。說心裡話,她已經八十有餘,臉上皮膚下垂,臉龐輪廓也已不分明,眼角的魚尾紋堆積如雲,使深陷的眼睛很幽深,不似年輕人那般清亮明朗。
可是,不得不承認,張奶奶——身上確實有一種超乎年齡的明媚,還有舉手投足間的優雅,令你感受到一種美。我於是老老實實點頭說,很美。她笑了。我也很奇怪,她從不像一般老人此刻會有的謙虛,不行了,老了之類的話,她從不說。
我對張奶奶年輕時候很感興趣,回宿舍跟同學問起,她說姑奶奶以前是經營美髮店的,可能因此對形像很重視吧,她說。可是我不以為然,總覺得老太太不是重視形像那麼簡單,她的內心散發出某種令人景仰的力量。
家裡吃飯只有我們兩個,可是無論是喝咖啡,還是吃蛋糕,她都會盡力把手放穩,不把咖啡潑到外面,蛋糕也不會掉得哪裡都是蛋糕沫。她坐在窗前的沙發上看書,姿態很優雅,儘管我覺得也許她把腿放在茶几上會更舒服。
我有時甚至想,是不是因為我在場,老太太放不開,我延長到別的房間打掃衛生的時間,可是偷偷看,她還是那個姿勢,我發現如果累了,她寧可拄著拐杖站起來動一下,也不會隨意伸腰拉胯,毫無形態。
由於腿部疾病,她幾乎足不出戶,可是即使睡袍,也是每日更換,妝畫得一絲不苟。我初來乍到,對於她的口味還摸不清,但她從不抱怨,只是在餐桌上教我,黑米蛋糕要怎樣烘焙,水晶豆沙放多少合適,那麼久也沒看過她發怒,或者說出狠狠的話,就像一脈溫泉靜靜地淌在每一個波瀾不驚的日子裡。
因此我相信了,有些人,優雅已成為生命的底色,並不是刻意為之,無需在人前故意如此。
讀大學四年,我照顧老太太三年,第四年兒子接她去了國外。我覺得這三年我在老太太身上得到的不光是薪酬,還有骨子裡的優雅。精緻對待自己,不抱怨,寬容,善良,熱愛學習和閱讀。我也相信了,一個人的高貴優雅其實和財富地位沒有絕對的關係。
之後我也接觸過一些被稱為貴婦、名媛的人,她們私底下都不是那麼有修養,跟在大眾面前是完全顛覆的形象。
人至中年,已經顯現按耐不住,此生多勉強,此身過巔峰,真正做到內心優雅淡薄,不焦不躁的有幾人?還看到一些新聞說,老人對不讓座的人責罵甚至毆打,心中就想起張奶奶。
一個人於無人見處的優雅,甚至是一種慎獨,也可以說是一種勇敢,因為它跨越了太多磨難,原諒那麼多醜陋,還是看到花開。在漫長而磨難叢生的歲月裡保留柔軟和溫度,保持優雅,絕對堪稱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