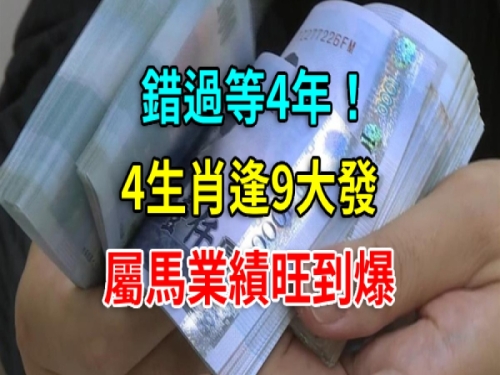母親懷孕想死,卻被畸形男救活,開啟我們的悲傷故事!

1
我父母雙亡,大學的時候,我藉此換了不少錢。每每從禿頂的校領導手裡接過貧困補助的時候,我眼眶發紅,心裡想的卻是,這大概是我父母能留給我的為數不多的東西了。當然,我很感激他們。
我的母親是個妓女,我也不清楚她的年紀,她不到20歲就懷了我,但不知道我是誰的種。她想尋死的時候,被一個鐵道修理工從鐵路上拖了下來。
後來她就和那個鐵道修理工住到了一起,我叫他父親。
我的家鄉是一個很小的城市,我的家就在鐵道旁,每天上學都要穿過鐵道。鐵路旁邊有很多磨得圓滾滾的小石頭,學校裡的孩子都喜歡撿這種小石頭當玩具。
父親從來不讓我撿,好像我在鐵道旁邊停留久了,就會被火車撞飛。
雖然我不是他的親生孩子,但是他對我管教很嚴。
2
父親每天背著扳手和錘子沿著生鏽的鐵軌走,不時停下來敲敲打打。他好像從很小的時候就乾這個工作了,工資少得可憐,但是他也做不了別的。
他先天畸形,長得很高,極瘦,雙腿像竹竿一樣,腳很小,走起路來兩條腿向裡湊,身子一顛一顛的。左手手腕只能向外翻著,常年插在口袋裡,什麼都乾不了。
這是天生的病,治不了。畸形雖不嚴重,也有異於常人,尤其是在小孩子眼裡。我經常看見小孩用彈弓把那些圓滾滾的小石頭打向他,有時候還會打向我。他們大聲地叫我“小殘廢”。
我恨他們,也恨父親,我恨他為什麼要救母親,害得我還要來到這個偽善的世界。
父親說,我剛出生的時候,母親很長時間不說一句話,每天不知道流多少眼淚。
有一天,她抱著我出去散步,一路上被人指指點點。那些人用故意壓低但足夠清晰的聲音罵她,罵父親,罵我是個雜種。母親沿著鐵軌一路跑,遇見一口枯井,就把我扔進去了。
父親那天把她打了一頓,半夜去把我撿回來了。
3
父親說我從來不哭,被丟在枯井裡也不哭,就像睡著了一樣,他還以為我死了。
在我還不滿一歲的時候,母親爬上運煤的火車跑了,當然沒有帶上我。父親為此多了一樁屈辱,連個婊子都看不住。幾個月後母親回來了,父親沒有說什麼,要是我,我也覺得沒什麼可說的。
此後的日子裡,母親經常會消失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父親好像也習慣了這事。只是隨著母親消失的次數,父親對她的態度越來越差。
直到母親回來的時候又懷了孕,她說這孩子是父親的。父親帶她去把這孩子流掉了,因為他怕自己的孩子也像他一樣。此後,母親就不消失了,開始洗衣做飯,對我也有了點母親的樣子,可能是認命了吧。
父親對母親的態度並沒有因此好一點,父親的心理好像因為我們的到來逐漸扭曲得厲害。
他對母親的態度很差,對我的態度也很差。從小到大,我聽到父親對母親說的最多的三個字就是“賤女人”。
他很喜歡用他直不起來的腿踹我。每次我不小心說了讓他不高興的話,他就一腳把我踹出兩三米遠,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用右手指著我大聲呵斥:“閉嘴!”母親這時就會一邊護著我,一邊哭。
4
隨著我慢慢長大,父親的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他好像一直在承受著莫大的屈辱,我和母親,別無選擇地成了他發洩的工具。
我們靠著父親微薄的工資生活,母親在家洗衣做飯,沒有工作。我上學之後,父親的工資顯然是不夠用了,有一天,父親幹完活回來,吃飯的時候母親跟父親要錢:“你再給我些錢,買菜做飯的錢不夠用了。”
父親叼著煙說:“賤女人,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錢。”“賤女人,給你的錢都花哪去了,他媽的多少天沒吃肉了。”
母親皺著眉說:“你也沒給多少,再說,孩子上學還要交錢,省著點花。”
父親當時火了,一下子掀了桌子。他歇斯底里地喊:“我掙得錢還不夠吃肉的?你算個什麼東西,別給我瞎打算。女孩上什麼學,上完了還不是要跟你一樣,賤女人,你要是覺得委屈就給我滾。”
母親什麼也沒說,她把那個沒破的碗撿起來放到一邊,然後開始收拾灑在地上的飯。父親依舊沒完,繼續嚷嚷:“你哭什麼哭,別在這齣這一副爛樣子給我看,趕緊給我滾。”
然後母親停下來,開始往外走,走的時候含著淚望了我一眼,我裝出一副很害怕的樣子看著她,眼裡也含著淚,透露出一種強烈的不捨,但是心裡卻想:快滾吧,快滾吧,走了就不用繼續這樣的生活了。至於害怕,我倒是已經習慣了。
母親終究沒有走,她在門檻上坐了下來,低著頭又開始哭。到了上班的時間,他出門的時候對母親說:“給我滾進去,別在這給我丟人。”然後父親就邁著他滑稽的步子走遠了,母親又坐在門檻上哭了好一會兒。
我走過去說:“別哭了,快進來吧,再吃點飯。”
他們倆的戲碼,我實在是看夠了,很無聊,也很無恥。
5
我從小就學會了表裡不一,我覺得人都很賤,至少我的父親是這樣。
然而,母親好像習慣了這樣,她越來越擅長忍氣吞聲,越來越擅長以一種別人難以覺察的方式抹眼淚。父親則變本加厲,他對母親的忍氣吞聲很不滿意,對母親的呵斥越來越頻繁,有時甚至拳腳相加。
每次,母親都能當成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我覺得他們都有些麻木了,而我隨著年齡的增長,卻感覺到內心有一種不安的成分滋生地越來越快。
有一次,學校開運動會,順便表彰一下優秀的學生。我那次考試考了第一,學校知道我的家庭情況,讓我的家長去做一次講話。這樣的父母都能教出第一名的孩子,學校藉此來鼓勵其他學生學習。我覺得很可笑,但是也沒法拒絕。
吃晚飯的時候,我說:“讓我媽去吧。”
我媽說:“讓你爸去吧。”
我就說:“還是你去吧。”
我爸突然把筷子拍在桌子上,朝我大聲喊:“嫌我給你丟人是不是?”
我不知哪來的勇氣,看著他說:“你以為不去就不丟人了?”
我母親拍了我的頭,趕緊說:“先吃飯,先吃飯。”
父親坐不住了,他把手裡的碗使勁摔在地上,抬起右手給了我一個響亮的耳光:“養大你就嫌老子丟人了?嫌丟人就給我滾!跟生你的賤女人一樣。”
我放下筷子就往外走,走到門口,母親就追出來,喊:“給我回來。”
我看見她在追,不自覺地跑了起來。那一刻,我想遠離這個家,再也不用回來。
6
那一晚刮很大的風,很冷,我抱著腿在麥地裡坐了很久,恐懼慢慢湧上心頭。我不是害怕一個人,我害怕再次面對父親時他會怎麼對我。那一刻,我深刻知道了我內心的懦弱,我只是一直在逃避。但是,大多數人都是這樣,不是嗎?
我的害怕沒有成為現實,因為父親死了。
我跑出來後,他一口氣喝了半瓶白酒,站在門口哭。母親回去後,他就讓她滾。母親說:“回去吧,她一會兒就回來了。”
他可能是醉了,也可能是瘋了,“你和那個雜種,你們都滾。”他咆哮了起來。
母親沒有理會他,進了門。他突然抓住母親的頭髮,一腳把母親踹了很遠。母親哭了,一句話也沒有說。
“你這個賤貨!我要殺了你!”父親又過去抓住母親的頭髮。
母親好像很害怕,身體顫抖,兩隻手在空中胡亂的甩,嘴裡喊著:“讓我去死,讓我去死。”
她不知哪來的力氣,一下把父親的手甩開。父親一個趔趄沒有站住,頭撞在廁所旁邊的石頭上,留了好多血。過了一會兒,沒氣了。
她像瘋了一樣,在麥田裡找到我,口齒不清地說,父親死了。我沒什麼不好的感覺,甚至有點高興,鬆了一口氣,我不用再想回去怎麼面對父親了,以後都不用再想了。
我替父親和自己感到高興,我們都活得很壓抑,這樣是雙向解脫。
她驚恐地說:“是我殺的,是我殺的,讓我去死吧。”
我說:“他死了是少受點苦,你們誰也不欠誰。”
但我在心裡想,你要去死的話我也不會攔著,所以我死的時候你也千萬別攔著。你們死了我不會感到難過,可能會替你們開心,因為換成我的話,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替我難過。
那天晚上,我把父親拖到鐵軌上,一邊拖一邊在心裡默念,“到那邊你過得比我們好。”
火車不會因為一點小事兒就停下來,父親的半截身子沒了。
父親以鐵道修理工的身份死在鐵道旁,國家賠了我們一筆錢。這筆錢母親不敢要,於是我來保管。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錢本來就是我的。要不我們怎麼活。
7
父親死後,我們的生活平靜了許多。
但母親精神出了問題,經常在睡覺的時候突然叫起來,哭。
沒事兒的時候,我喜歡在鐵道旁邊坐著,吹吹風,覺得身體空前的輕,有時候還會微微笑起來。在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我今後要怎麼做,怎麼活下去,但是父親的死好像讓我突然豁然開朗,我好像知道怎麼做了。
我快要找到出口了。
而母親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她的眼眶黑得嚇人,可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哭出聲來,比如做飯的時候,洗碗的時候。
父親還在的時候,哭對於母親來說是最好的釋放,那時候還要在意父親的心情,現在她終於能隨心所欲地哭了。雖然不知是為父親哭,還是為自己哭。所以從這一點來看,我覺得母親過得比以前好多了。
我不敢在她眼前提死人的事情,因為我怕她大喊大叫。漸漸的,她做的菜裡一點肉都找不到了,我們開始吃素。我懷疑她真瘋了。
有一天,附近有人家死了人,《安魂曲》響起的時候,她從椅子上突然站起來,圍著桌子不停地走,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右手握著左手,不知道轉了多少圈,最後跪在地上,抽泣了起來。
而我不知道說什麼,只能趕緊吃完飯去上學。
我在心裡咒罵著,老天爺為什麼要製造這樣的人生呢?
8
我相信母親不久就會變好,只需要一點點的時間。因為我想不通她竟然會為父親那樣的男人變成這個樣子,她根本不愛他,她曾經無數次拋棄我們。
果然,不久之後,有一個男人開始頻繁出入我家。那段時間,母親每天對著鏡子畫眉毛抹口紅,很在意自己的打扮。一天,那個男人來我家吃飯,母親做了很豐盛的晚飯,吃飯的時候,我突然說:“媽,你要找男人了?”
那個男人顯得很尷尬,我媽沒有想到我會這麼說,有些生氣,說:“是,我是要找男人,就是這個。你有什麼意見嗎?”我說:“我對你沒什麼意見,我對他倒是有點意見,他知道你是什麼人嗎?他知道我爸是怎麼死的嗎?”
她突然掉下眼淚,嚎啕大哭起來,隨即跑進了自己的屋子,那個男人也趕緊跟了進去。我心裡很高興,一是因為我媽驗證了我的想法,二是,看到這樣的場景,不知怎麼的,我就是很高興。
然後,我一個人,慢慢地吃我媽做的那頓豐盛的飯。
9
在我十七歲那年,母親和那個男人結婚了。那個男人和母親年紀相仿,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找母親這樣的女人,我想起電視上演的那些以感情騙錢的嘴臉,但是母親沒有什麼錢。
對於他倆的事情,我沒有反對,一是我沒有理由反對,二是我心裡隱隱地希望母親被這個男人再次拋棄。這是什麼心態呢,我也說不清楚。
可能我也瘋了吧。
那個男人對我很好,經常會買一些東西討好我,說真的,比我父親好多了。但是對於現在的我來說,我認為這是一種討好,我對他說:“你不用管我,管好我媽就行。”
有時候我媽會讓我叫他一聲爸,我就會說:“你還是少提這事好,你看他多尷尬。”那個男人就會尷尬地笑笑。我試圖了解這個男人的底線在哪裡,或許他曾想過和我媽好好生活,但是我希望他走。
三個月後,這個男人果然走了,沒有帶走什麼東西,也沒有讓母親懷孕。我不知道是他自己想走的,還是我把他弄走的,總之是走了,我有些開心。
母親一下子又回到父親剛剛去世時的樣子,整天不停地掉眼淚,我說:“你就是犯賤。”
母親沒什麼反應,繼續哭。我走出家門,來到鐵道旁邊,撿起一個小石頭使勁扔向遠處,對著經過的火車歇斯底里地大喊。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我想大概是從我父親死的那天晚上開始,我一個人在麥地裡坐著,覺得面對著空前的黑暗。
然後當我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突然感覺到前方某處有亮光,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抓住,誇張點說,那是一種求生的慾望。這些年,小心翼翼,唯唯諾諾,到今天,我覺得自己終於有大聲說話的勇氣了。
這件事情過去了半個月,母親慢慢好了起來,這次恢復的時間短,可見她不愛這個男人。
10
我感覺她一下子老了好多,變得遲鈍和更加沉默。她喜歡上了織毛衣,經常在一個地方坐很久,織毛衣的手機械地動著,眼神呆滯。她對我的關心倒是比以前多了,我想她可能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人了。
不久之後,她又開始往家裡帶男人,有時候每天一個,有時候兩三個。她把自己有些泛白的頭髮染成黑色的,穿上她喜歡的裙子,我才知道,她又開始賣身了。
我能理解她,人總是很輕易地在髮灰發黑的漩渦裡沉淪。我什麼都沒說,因為我崇尚公平,公平就是她愛做什麼就做什麼,我要做什麼她最好也一句話也別說。
那一次開家長會,我考得很好,老師讓她去。她說:“不去了,給你丟人。”我突然想起父親去世那天吃飯的場景,覺得時間真會開玩笑。我對她說,“還記得嗎,我爸死的那天,好像他很想去給我開家長會呢。現在他死了,你就代他去一次吧。”
她呆了一會,眼淚順著臉滑下來。我突然發現,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她哭過,很久沒有跟她說過什麼,甚至很久沒有正眼看她。
那天她穿的很樸素,一副精神恍惚的樣子。過鐵道的時候,她牽起了我的手,我很厭惡這樣,但是我沒有掙脫。我擔心她會一下子暈倒。
說真的,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讓她去,可能是期待一種很尷尬的效果,我想讓她難堪?
我的成績好,母親被叫起來給其他家長談一下教孩子的心得,其他學生的家長就看著她意味深長地笑。
她顯得很惶恐,甚至很難把頭抬起來,她說:“我沒有教什麼,都是她自己學的。”然後,就坐下來,不說話了。那一刻,我突然心裡湧上快感。
結束的時候,她走在我前邊,唯唯諾諾的,我覺得那一刻,她可能是需要我的。我能感受到周圍的男男女女異樣的眼光。那種眼光,讓我想起了他們看我父親的眼光,摻雜著多種不明朗的情緒,比如同情,嘲笑,厭惡,當然還有鄙視。
11
走到校門口的時候,我清晰地聽見一個男生喊了一句“賤女人”,然後周圍的人哄笑起來。
“賤女人”,我好久沒有聽到這三個字了,我真該謝謝他。
我轉過頭看著他,他發笑的面孔讓我與小時候看見的用彈弓打父親的孩子的面孔契合起來,心裡一陣噁心。
他說:“看什麼看,賤貨,你媽多少錢一次?她怎麼把你教的這麼好,哈哈,你的活是不是也不錯呀,哈哈?”
然後,他周圍的人就笑得更厲害了。我內心突然湧上一股強烈的衝動,血液翻騰起來,就像我在過鐵道的時候感覺要飛起來一樣,我覺得自己圓滿了。我從地上撿起一塊磚頭,然後走到他面前,狠狠地拍在他的頭上。
我媽當即癱在地上。
這件事我很後悔,我怎麼會為她這麼衝動呢,差點破壞了我的計劃。
那個男生傷得併不嚴重,但是他家里人卻鬧得很厲害。我沒有看到,只是聽說母親在校長辦公室裡跪了好久,不知用了什麼方法,我沒有被開除,也沒有賠多少錢。
那個時候我挺害怕的,不是害怕我做了讓人害怕的事情,是害怕我不能繼續上學了,那樣,我就沒法離開這裡了。
此後,學校裡的人都避著我,我不知道有意還是無意,只是覺得可笑。不過,這樣挺好的,沒有人打擾,我可以一個人安靜地學習,積攢力量,我很喜歡。
十九歲那年,我考上了一所外地的大學。那個地方離小城很遠,坐火車要兩天兩夜,經常下雪。
母親問我:“你幹嗎要去那麼遠。”我很無情地說:“我想離這個地方遠點,我怕還是有人認識我。”母親聽了,就低下頭,繼續織她的毛衣了,我不確定她有沒有哭。
我走的那天,母親做了幾個菜,我們還喝了點酒。那天母親一直笑,我也一直笑。我很開心,我不知道母親是不是。
她送我去坐車,抱著一個瓶子,瓶子裡是她煮的茶葉蛋。她跟我對視著沉默了一會兒,我知道她很想說些什麼。當她剛想開口的時候,我說:“我上車了,你回去吧。”然後我就拖著箱子,抱著瓶子上車了,沒有回頭看她。
我不知道母親是什麼表情,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笑,或是哭。管他的呢,天知道我有多麼憧憬這次別離。
火車開了一會兒,我右手提著那個裝滿茶葉蛋的瓶子,伸出窗外,停了幾秒,鬆開了。
我打開左手,是上車前我撿起來的圓滾滾的小石頭。我希望自己像它一樣,被時間和傷痛打磨成圓的,誰也看不出什麼,雖然內心還是坑坑洼窪滿目瘡痍。
12
就像我計劃好的那樣,我很少再回到那個小城。雖然那裡有我想忘也忘不掉的回憶,那回憶很髒,不想再去觸及。中秋節的時候,母親打電話過來,問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說,不回去了,太遠,然後就是長時間的沉默。
掛電話的時候,我突然對她說:“媽,你再找個男人吧。”我媽說:“好,不過誰還要我。”
那是我最後一次跟母親講話,不久之後我就接到鄰居的電話,告訴我,母親自殺了。她給我留了一封信,我沒有看,直接扔掉了。
我在心裡說,我已經不是我了,還有什麼值得看的呢。我恨父親,恨母親,甚至有時候會恨所有人,其實我是個很脆弱的人,他們卻沒有讓我體會到一點溫情,只會時常讓我感到崩潰。
我只能逼迫自己習慣冷漠、痛苦和悲涼,我怕成為像母親一樣的女人,特別怕。我擅長察言觀色,學習人們的卑鄙和偽善,並以此來對待周圍的人,報復他們,也報復自己。
這樣的話,他們就能知道我所承受的痛苦了吧,這樣的話,我就會習慣這些痛苦了吧,我以後就不會再害怕什麼了吧。
而這一切,到現在,只是一個故事而已。
我突然覺得,我們真是個可憐的家庭啊,多麼讓人同情的三個人啊。於是,在申請貧困補助的時候,我輕而易舉地獲取校方的信任。他們只知道我父母雙亡,而我的故事,還埋在我心裡。
我終於實現了自己的計劃,過上了想要的生活,煢煢獨立,沒有任何人和我有關係。我只需關心自己的存活,多麼值得慶幸呀。
這讓我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
很久之後,我再次回到了這座充滿回憶的小城,見母親最後一面。是不是真的想見,我也不知道。她是吃安眠藥自殺的,死的時候穿著她最喜歡的裙子,很安詳。
我覺得她在那邊,一定過得比這邊好。這麼想,我真的很難露出悲傷的表情。
在小城的那個夜晚很難睡著,我就在外邊閒逛,然後穿過鐵道,不知不覺走到父親死的那天我藏身的麥田。我走過去蹲在裡邊,長得很高的麥子也遮不住我的腦袋了。空曠的田野上,漫天遍野的黑暗向我壓過來,好像一個巨大的、深不見底的漩渦。
我突然害怕起來,應該沒有什麼可害怕的,但是還是害怕,空前的害怕。我根本想不起來上次哭是什麼時候了,而現在,竟然淚流滿面。
終於,我和所有的人都成了陌生人。
這悲傷的故事,希望你能分享出去,因為在世界的某個角落,真的有人這樣活著。